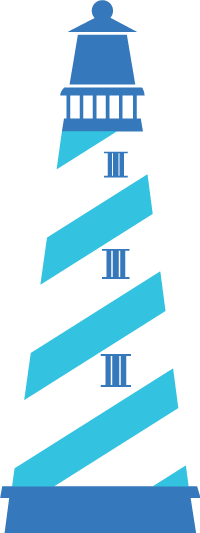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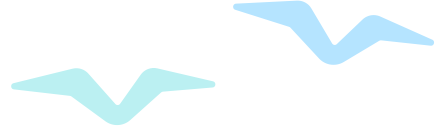

点击上方“武大边海”直接订阅


李克强出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
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本文作者
何艳梅
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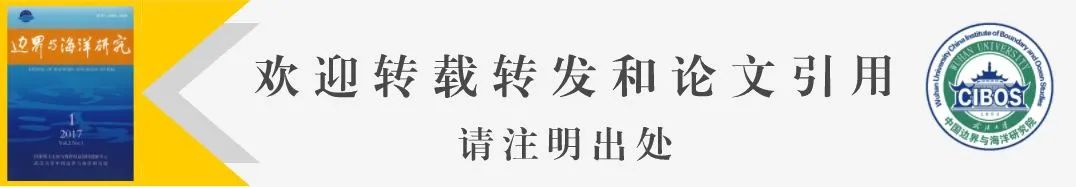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6期,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原文下载链接。

一、国际河流航行利用的管理体制
国际河流航行利用管理体制的正式建立起源于莱茵河。为了促进莱茵河航运与贸易的发展,法兰西帝国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根据1804年缔结的关于对在莱茵河航行的船舶征收通行费的条约,成立双边的莱茵河委员会,负责对莱茵河航行的船舶集中征收通行费,用于改进河流可航性和曳船道状况,也有权解决针对征收通行费的法规而产生的争端。莱茵河委员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跨国流域管理机构和区域性国际组织。1815年重新瓜分欧洲版图的维也纳公会通过的《维也纳公会最后文件》,继承和发展了法德之间建立的莱茵河航行利用的双边管理体制。根据该公约附件16(B)的规定,由莱茵河沿岸国任命委员共同组建多边的莱茵河航行中央委员会,接替莱茵河委员会,继承其行政管理权。
《维也纳公会最后文件》的缔结、实施和莱茵河航行中央委员会的成功运作,推动了国际河流航行利用法的初步形成。在莱茵河之后,陆续有其他欧洲国际河流的沿岸国和地区大国签订条约和建立流域管理机构,对国际河流的航行利用开展共同管理。随着国际航行事业的发展和流域管理机构工作的开展,这些国际河流逐渐形成了复杂的航行规则,国际水法在此基础上正式形成,国际河流航行利用管理体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事实上,在《维也纳公会最后文件》实施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从国际社会通过的涉水国际条约、软法文件和司法判决,可以看出国际水法的基本内容是国际河流的航行规则以及缔约国对联合管理机构的授权。 在国际河流航行利用法的发展框架下,由莱茵河沿岸国开创,多瑙河、奥得河等欧洲国际河流沿岸国发扬光大的航行利用管理体制,先后移植和借鉴到非洲、北美洲、亚洲等地区的许多国际河流。
二、国际河流非航行利用的管理体制
19世纪末以降,随着西方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繁荣和人口膨胀,国际河流沿岸国对水电开发、农业灌溉、防洪等水资源非航行利用的需求日益增长,也使沿岸国之间产生了公平分配、合理利用水资源等竞争性问题及相关冲突。在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这些问题和冲突的过程中,产生了绝对领土主权、绝对领土完整、在先占用主义、限制领土主权等不同的国家水权理论。由于限制领土主权理论兼顾了不同沿岸国的利益和需求,因此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理论。许多沿岸国以此理论为指导,通过谈判建立了关于国际河流水量分配、水电开发、洪水控制等非航行利用的条约框架和管理体制,并在条约实践和有关软法文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公平和合理利用、不造成重大损害、信息交流等习惯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推动非航行利用管理体制在全球许多跨国流域陆续建立。
国际河流非航行利用条约肇始于19世纪,非航行利用的合作管理体制则起源于美国与加拿大1909年签订的《界水条约》及其建立的常设联合管理机构——国际联合委员会(International Joint Commission,IJC)。美加《界水条约》在全球创立了流域管理与国家管理相结合的非航行利用管理体制,尤其具有革新性的是对IJC的授权。根据条约规定,IJC享有监督两国对水的利用、对跨界事项进行调查、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等职能。成立100多年以来,IJC根据《界水条约》和缔约国的授权,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预防和解决了美加两国之间的许多界水争端,也促进了国际水法原则和规则的发展。由于美加《界水条约》及其创立的联合管理体制行之有效,在墨西哥与美国的界水管理中也得到运用。
随着国际河流非航行利用的繁荣和国家间纠纷的增多,20世纪以来由政府间组织和国际法学术团体通过的许多国际法律文件,对作为非航行利用基础和保障的限制领土主权、公平和合理利用、不对他国的利用造成损害、合作管理等理论、原则和规则多次进行承认和强调。尽管这些文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呼声、国家的意愿与承诺,并且“已经逐渐渗透到当代的国家实践中”,陆续促进了以美加《界水条约》和IJC为样板的国际河流非航行利用条约框架与管理体制普遍拓展适用于全球其他国际河流,使国际水法从单一的国际河流航行利用法拓展到非航行利用法,并成为国际水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尤其是IJC被奉为双边联合管理机构的“圭臬”。
目前,世界各大洲界河或多国河流的沿岸国普遍缔结双边水条约并建立联合管理机构,主要负责管理两个缔约国之间的边界或跨界河流的非航行利用,并且通常具有信息交流、技术研究、水量分配的监督等职能,有的机构还具有解决争端的职能。亚非拉地区某些多国河流的沿岸国,依据签署的多边条约建立了联合管理机构甚至是全流域管理机构,负责管理某流域流经缔约国的河段甚至是整个河流流域,并通过研究、协调、建议等促进地区经济开发和沿岸国经济发展。随着沿岸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合作的加深,亚非拉地区某些仅仅建立了双边或局部流域条约框架和管理体制的多国河流,建立起了全流域条约框架及相应的管理体制。比如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所有6个沿岸国在中国倡导和组织之下,通过《三亚宣言》建立了全流域的澜湄合作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条约框架与管理体制之下,联合管理机构的职能、管辖范围及其所体现的沿岸国之间的合作程度有所差异,运作效果也有良莠之分。总体来看,欧洲的边界或跨界水管理机构更接近于IJC,具有较大的管理权限,体现了沿岸国对流域管理与国家管理的并重;亚非拉地区的许多双边、多边或全流域管理机构只有研究、咨询、建议、协调等技术性职能,缺乏实质性管理权限,仅仅是沿岸国国家管理的辅助或补充,说明沿岸国之间的合作还处于较低层次。另外需要注意,亚非拉地区许多跨国流域多边条约框架的形成和多边管理机构的设立与运作,都有国际组织或流域外大国的援助。由于主要是为了捐助而建立的管理体制,没有考虑或结合流域自然条件、沿岸国政治关系、经济制度差异等,因此运行绩效普遍较差。反倒是有些双边管理机构,由于双边合作的针对性、灵活性和便捷性,更容易取得较好的管理绩效。
三、跨界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
20世纪以来,西方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国际河流的污染,也引起了沿岸国的关注,并经由软法文件和司法判例的推动,国家实践中逐渐确立了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以此原则为基础,跨界水污染防治法及其框架下的污染防治管理体制得以形成,并在国际环境法的推动下获得较迅速的发展。大体而言,跨界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包括一般性体制和专门性体制两类,后者通过生态系统方法的引入取得了明显的管理成效。
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最初仅着眼于保障每个沿岸国对跨界水资源的公平和合理利用,要求一国的开发利用行为不对他国利用、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因此在跨界水污染防治法形成的初期,国际水条约普遍将污染防治作为非航行利用管理体制的附属部分。非航行利用条约即使涉及到防止和消除污染的规定,也多为一般性的政策宣示,缺乏诸如水质标准、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等关于防止污染的实质性措施条款。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沿岸国缔结的关于或主要是关于跨国流域非航行利用的大量双边条约,普遍规定了缔约国预防跨界水污染的一般义务,并由缔约国联合建立的非航行利用管理机构协助国家履行这些义务。
1941年美国与加拿大关于特莱尔冶炼厂空气污染案的仲裁裁决,首次在国际环境法上确立了国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对他国造成损害的原则,促使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开始融入了环境保护的元素。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人类环境宣言》为里程碑,国际环境法开始形成,推动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发展成为一项不对他国和国际水道造成重大环境损害的、适当审慎的义务。它要求沿岸国采取防控跨界水污染的适当措施,诸如制定和实施规制公共和私人行为的法律和规章,或者在流域层面联合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签署和实施有关污染防治的条约,设立联合管理机构以促进信息交流、制定污染防治规划、设立水质标准、开展水质监测、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等。近些年来签署的非航行利用条约也相应地发展为规定水质标准、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等防治跨界水污染的实质性措施条款,并由非航行利用联合管理机构负责污染防治事宜。
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由于工业复兴而造成的跨界水污染形势日益严峻,开始尝试建立专门的管理体制以有效治理跨界水污染。泛欧洲、北美洲地区许多边界或跨境河流的沿岸国,较早通过签署防治水污染的专门性双边条约,在流域层面建立了专门的污染防治管理机构,或者将现有非航行利用管理机构的职能扩大到污染防治。专门性跨界水污染防治多边管理体制的系统建立则始于莱茵河流域。为了有效解决莱茵河的污染问题,瑞士、德国、法国、卢森堡和荷兰等五个沿岸国于1950年专门建立防止莱茵河污染国际委员会。1963年《关于防止莱茵河污染国际委员会的协定》(《伯尔尼协定》)的签订,为委员会的运作提供了永久性法律和制度框架,从而在全球正式开创了多边流域管理与国家管理相结合的跨界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亚非拉地区的国际水条约框架与管理体制以水量分配、水电开发、洪水控制等非航行利用为主,鲜见专门性污染防治管理体制。“非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界河流的专门性污染防治管理体制,因为它是在两国关于跨界河流利用和保护伞式协议的框架下建立的。
早期的跨界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着重对跨界水污染的消极治理或“个案”解决,因此成效甚微,直至受到生态科学发展的影响和国际环境法的推动,运用了生态系统方法,把跨国流域地表水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进行治理,才明显改观。最早运用生态系统方法的是五大湖流域。1978年《大湖水质协定》是最早规定维持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国际条约之一,其第2条规定条约的目的在于“恢复和维持五大湖流域生态系统的化学、物理和生物完整性,”可以说拉开了新时代跨界水生态保护法的序幕。在莱茵河流域,经过沿岸国多年治理,莱茵河水质未有明显好转。直到1986年9月发生的瑞士桑多斯化学污染事故使莱茵河受到重创,防止莱茵河污染国际委员会的最高决策机构部长级会议1987年重新制定《莱茵河行动计划》,引入生态系统方法,莱茵河水质才得到明显改善。
四、跨国流域综合管理体制
“流域”概念在19世纪后半叶就出现在国内法中,“国际流域”的概念是结合“流域”的概念,从国际河流和国际水道的概念发展而来的。国际流域概念的提出和外延的拓展,使公平和合理利用、不造成重大损害、共同利益等理论和原则注入了生态系统保护的内涵,也是对国际河流概念和国际水法体系的重大突破,为综合管理体制的建立、跨界水资源的全面开发利用、生态系统保护创造了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20世纪末以来,以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为引擎,经由《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一系列多边环境条约的缔结和实施,联合国国际法院所审理和判决的多瑙河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大坝案的推动而迎来发展高潮的国际环境法,逐渐从占统治地位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变为以生态保护为中心,并将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保护、风险预防、环境影响评价等理念、原则和制度融入国际水法原则、规则和制度。
水资源的综合管理是实现跨国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保护的基础,这是《21世纪议程》《都柏林宣言》《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行动计划》《柏林规则》等国际社会近些年来通过的许多法律文件的共同结论。而建立流域管理机构,赋予其相应职权,是促使流域国更好地履行公平和合理利用、不造成重大损害义务,促进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关键和根本。在国际环境法的新发展和上述文件的共同推动下,以及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水文科学和生态科学发展、地区和国家实践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下,跨界水生态保护法作为国际水法的新发展,推动了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跨国流域多层综合管理体制的建立,尤其是在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洲地区和南共体地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区域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使跨界水资源管理在欧洲区域甚至全球层面展开。联合国欧经委1992年通过的《赫尔辛基公约》,2000年欧盟通过的《水框架指令》等区域性水条约,可以说是泛欧洲和欧盟地区的伞式协议,它们同时适用于地表水和地下水包括封闭地下水,充分贯彻或体现了流域生态系统方法。泛欧洲和欧盟地区跨国流域的沿岸国在这些伞式协议的框架下缔结和实施流域双边或多边条约,建立和运作流域管理机构,从而形成了区域管理、流域管理、国家管理相结合的综合管理体制。随着《赫尔辛基公约》演变为全球性条约,正式形成了全球性管理体制。在全球、区域和流域条约的框架下,全球、区域、流域、子流域、国家、地方等各层次的管理机构各司其职、相互协调、通力合作。比如欧盟《水框架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制定统一的跨国流域管理计划,这一规定在近年欧盟国家之间签署的流域水条约中得到了贯彻。《萨瓦河流域框架协定》就是在多瑙河和整个欧洲实施《水框架指令》的典范。即使是早期签署的条约比如《多瑙河公约》《保护莱茵河公约》及其建立的管理机构,在实施和运作中也都认真执行指令的规定。欧盟甚至是《多瑙河公约》《保护莱茵河公约》《保护斯凯尔特河协定》等流域条约的缔约方和依条约建立的流域管理机构的成员方。此外,欧盟成员国通常设立国家委员会,负责协调国家与流域机构的工作,以更好地实施《水框架指令》和其规划条款。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下简称“南共体”)是非洲地区最成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南共体的14个成员国借鉴国际法协会《赫尔辛基规则》和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编纂成果,于1995年签署并于2000年修订了《关于共享水道系统的议定书》,适用于共享水道的航行利用、非航行利用、污染防治和生态系统保护。缔约国在这一区域水条约的框架下缔结和实施流域双边或多边条约,建立和运作流域管理机构,从而形成了区域管理、流域管理与国家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国家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程度、区域一体化水平、流域自然条件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南共体地区与泛欧洲和欧盟地区的管理体制有很大不同。首先,泛欧洲和欧盟地区的流域管理机构享有制定和实施流域管理计划、拟定水质标准等实质性的管理权限;南共体地区的流域管理机构一般仅有信息交流、提供咨询、组织会议等技术性权力,只是对国家管理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其次,泛欧洲和欧盟地区许多沿岸国水量相对丰沛,流域水问题主要是污染防治和生态系统保护,而且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一体化程度、国家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程度较高,因此可以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真正实现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和水量的综合管理;南共体地区的管理体制则仅仅实施了地表水体的航行利用、非航行利用、污染防治等相对综合的管理,而且由于各沿岸国普遍的水短缺和经济落后,侧重于水量分配和经济开发。
五、跨界含水层管理体制
全球现有448条跨界含水层和含水层系统,随着国际水法及其各种管理体制和规制工具的发展,以及对地下水资源的质量和可抽取量的日益关注,规制和管理跨界含水层利用和保护的跨界含水层法及其框架下的管理体制正在引起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由于共同含水层国各自的法律体系、规则、制度和机构不足以提供预防和解决共享地下水争端的方案,有必要建立规制跨界含水层与跨界地下水开发利用和保护行为的国际法律体制。而且,即使某含水层是跨国流域的组成部分,可适用的法律体系、规则和制度也不同于规制跨界地表水的法律体系、规则和制度,因为含水层还包括不与任何地表水相联的跨界封闭地下水。随着《赫尔辛规则》《国际地下水规则》等国际文件对国际流域概念的提出和外延的拓展,以及适应含水层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客观需要,国际社会也通过了一些涉及或关于跨界含水层与跨界地下水利用和保护的法律文件和规则草案。这些文件影响着和渗透进国家的实践,促进了数个专门性跨界含水层条约框架及管理体制的建立,也标志着作为国际水法分支的跨界含水层法正在形成。
从全球各大洲情形来看,除了泛欧洲和欧盟地区通过《赫尔辛基公约》《水框架指令》及其框架之下的流域条约和建立的联合管理机构,实施地表水与地下水综合管理之外,与目前已发展成熟的跨界地表水条约框架、法律规范和管理体制相比,其他大洲和地区跨界地下水条约框架、法律规范和管理体制相当滞后。许多国际水条约及其框架下的联合管理机构仅仅规定和实施了利用和保护地表水的详尽规则,地下水仅在作为地表水污染的原因即成为地表水质的威胁时处理,而不是作为受保护的资源进行管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家对丧失领土主权的担心,跨界含水层法律和政治的复杂性,不同国家法律体系和资源开发政策、地下水抽取和污染控制方面的巨大差异等。规制共同含水层国之间关系的特定条约的缺位,更加剧了这种情势。
六、总结与展望
随着航运事业的发展、工业化的推动、水文科学的进步、国际流域概念的提出、生态系统方法的运用和国家政治关系的改善,全球跨国流域管理体制从无到有,持续演进,不断拓展,日益健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管理体制覆盖的地理范围不断延展,从早期集中于欧洲和北美,发展到非洲、亚洲和中南美洲,而且在亚非拉地区方兴未艾,或者说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其次,管理体制适用的活动领域不断拓展,从19世纪早期起步并局限于航行利用,到20世纪初扩展到水量分配、农业灌溉、水电开发等非航行利用,再到20世纪中期开始重视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20世纪末泛欧洲、欧盟、南共体等地区跨国流域开始迈向遵循流域生态系统方法的综合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第三,管理层次日益多元,逐渐形成从双层到五层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合作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尤其是泛欧洲、欧盟、北美和南共体地区在常规的流域管理和国家管理之外,适当地开展地方管理、区域管理甚至全球管理;第四,运作效果逐渐显现。跨国流域管理体制的建立和运作促进了沿岸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区域稳定与安全。
尽管取得了很多发展成就,但是亚非拉地区的多国流域和跨界地下水在建立或优化管理体制方面还面临着许多挑战:首先,许多多国流域缺失管理体制;其次,已建立的管理体制以碎片化的“功能性方法”为主;第三,跨界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综合管理进程缓慢;第四,许多流域联合管理机构的运行效果不理想。总之,作为国际水法中的组织法和管理法,跨国流域管理体制需要随着国际水法的发展而发展,也需要通过自身的发展推动国际水法的发展。这种发展需要流域国克服非合作博弈的零和思维,秉承流域利益共同体的信念,独立自主地建立和实施综合管理体制。从欧洲和北美的成功实践来看,对某一跨国流域的所有流域国来说,使其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是缔结和实施一项符合流域生态系统方法和现代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内容上相对综合的流域条约,建立综合性流域管理机构,赋予其规划、协调、管理等广泛的职权。以此标准衡量,全球尤其是亚非拉地区跨国流域的管理体制任重道远。
我国可以借鉴和吸取全球跨国流域管理体制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我国各跨国流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状况,与各共同沿岸国的政治关系和合作程度等,为国际水法和跨国流域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做出“中国贡献”: 一是在现有流域水条约和相关管理体制机制框架之下,深化与周边国家的跨界水合作;二是在缺失合作管理体制的跨国流域,与共同沿岸国通过谈判与协商,签订流域水条约、协议或宣言等,合作创立流域委员会、专家组等常设性或非正式的流域管理机构;三是与共同含水层国就跨界含水层和跨界地下水的利用和保护问题达成条约,建立专门的跨界含水层管理机构或者拓展中哈、中俄、中蒙联合水委员会的职能范围,开展制度化、常态化的跨界含水层和跨界地下水合作,或者达成非正式的、更灵活的双边安排。
END
编辑 |付姗姗
排版 | 李 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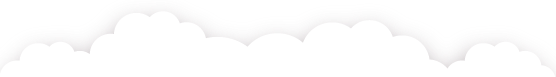

“武大边海”是边界与海洋问题最专业的信息平台
推送最新边海资讯、边海观察,发布边海问题专家观点
面向公众普及宣传边海知识
微信投稿邮箱:cictsmr@whu.edu.cn
“武大边海”独家授权转载《边界与海洋研究》期刊论文
期刊投稿邮箱:bjyhyyj@whu.edu.cn
编辑部联系电话:027-68753503
《边界与海洋研究》国内邮发代号:38-455
国际邮发代号:C9291
更多资讯请关注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官网:
http://www.cibos.wh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