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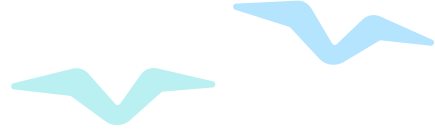

点击上方“武大边海”直接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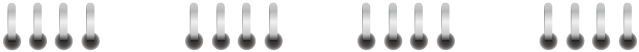

G20峰会达成“蓝色海洋愿景”。图片来源:中国海洋报
本文作者
王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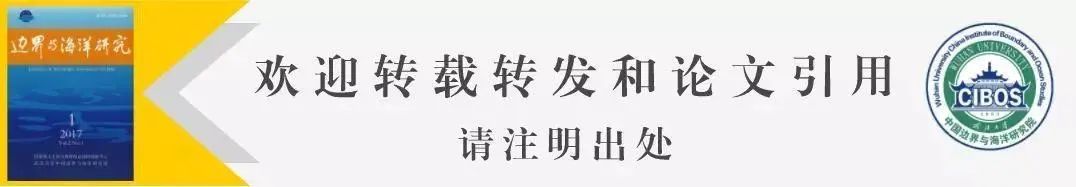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1期,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原文下载链接。

一、日本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理念渊源
第一,地理属性:四面环海、依海而生决定了日本“海洋国家”的定位。自古以来,海洋一直是日本对外交流的重要甚至唯一通路。海运长期占日本运输总量的99.6%,海上交通线成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日本国土面积仅38万平方公里,但其宣称的海域管理面积达到447万平方公里,日本试图利用地理优势和强大的能力储备,从海洋寻找国家振兴新的突破口,全方位地挖掘“海洋国家”的优势。第二,文化属性悠久而丰富的与海共生的“海洋文化”内化为日本人的民族自觉。日本对海洋的认知与对人海关系的思考贯穿于千年文化中,神话传说中日本国家与天皇王权的“起源”与海洋渊源甚深。不仅是神话,海洋在日本文学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海洋更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正因为“捕鲸是日本传统海洋文化的一部分”,日本才执意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并重启商业捕鲸。1996年,“海之日”重新成为日本国家法定节日之一,主旨是“感谢海的恩惠,同时也祈愿海洋国家日本的繁荣”。第三,民族特质:武力扩张型海洋战略的失败促使日本转向现代化海洋外交。向海对岸拓展的“登陆”意愿、控制海上通道的“安全诉求”与尚武、崇拜强者的民族特性融合,促使日本在历史上多次进行以武力谋求海洋霸权和掠夺陆上利益的尝试。至近现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再次选择以武力打开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二战中,日本谋求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其海洋野心膨胀到极点。而太平洋战争的结局宣告了日本武力扩张型海洋战略的彻底破产,这也成为日本由“强权与掠夺性外交”转向现代海洋外交的起点。
二、日本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法制与政策准备
(一)目标演进:参与全球海洋治理逐步深入,服务于“政治大国”诉求
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经济中心”导向型、酝酿转型与新目标确立、“大国化”目标导向等几个阶段,其对海洋战略的谋划亦与国家战略共振。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达到战后以来的顶点,大国意识复苏进而膨胀,谋求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愿望日渐强烈。2007年,日本通过《海洋基本法》,规定“国际协调的重点是在国际秩序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日本的主导作用”。2013年,安倍政府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确立国家战略及日本版“国家利益”,指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安全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强化美日同盟”频频被提及,被视为确保日本“国家利益”的目标与手段。
(二)法制保障:以立法的形式确立“海洋立国”的国家战略与全球海洋治理理念
被誉为日本“海洋宪章”的《海洋基本法》指出,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应以“海洋立国”使海洋战略以法律形式被确立为国家战略。日本还通过了《海洋建筑物安全地带设置法》,尝试以国内法拓展海洋权益。该法中关于“海洋建筑物”的定义与“安全地带”的地位、授权等规定,明显超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沿海国管辖权的范围。在东北亚海域,日本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邻国均存在领土主权争端。2010年“撞船事件”后日本对中国船长的非法判决以及2012年对钓鱼岛非法“国有化”的闹剧,实质上同样是日本欲以国内法解决有关问题的尝试。
(三)体制建设:成立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统筹国家海洋事务及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合作
为改变“九龙治海”的局面,《海洋基本法》对国家的海洋管理体制做出新的安排,内阁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以下简称“本部”)。本部成立以来,向上向本部长即首相汇报,首相参加每年1—2次的本部大会,为国家海洋战略确定方向;本部向下与各省厅协调,每年出台国家涉海预算,并结合《海洋基本计划》发布《海洋状况与海洋政策落实情况年度报告》,实现了海洋内政、外交事务管理向统筹有序、权责明晰方向迈进。
三、日本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路径与主要实践
(一)海洋“价值观”:树立国家形象,以所谓“普世价值”与“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扩大“朋友圈”
二战后,日本一直力求通过“价值观外交”聚合所谓海洋民主国家联盟,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所鼓吹的“钻石菱形构想”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可谓是对以“海洋”与“价值观”为抓手的日本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018年,日美公布“印太战略”合作文件,确定重点合作领域为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海洋安保与防灾减灾等,并将东南亚、南亚、南太平洋等区域的“海洋国家”列为“合作对象”。日本惯以所谓“国际规则”与“法治”切入多边外交,伺机扩大影响力与玩弄大国制衡。中日钓鱼岛主权领土争端升温后,日本向美国寻求关于“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承诺,支持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的南海立场,将东海、南海局势相提并论,拉拢英国、法国等域外国家关注太平洋与东亚海洋局势,将鼓吹“中国海洋威胁”和“牵制中国”奉为外交目的。值得关注的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和“海洋法治”被2018年出台的第三期日本《海洋基本计划》列为政策重点选项,预计它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日本着力推广的价值观旗帜。
(二)航道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日本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优先选项
作为资源贫乏的岛国,对外经济联系依赖漫长的海上运输,海上通道的安全一向是日本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中最脆弱的部分。为确保“海上生命线”的安全顺畅,日本在航道数据掌握、反海盗、经营与航道沿岸国关系上最为投入,以马六甲与索马里海域最具代表性。日本长期将对沿岸国的援助作为政策抓手,“软(实力)硬(实力)兼施”,在提高航道掌控力的同时,较为成功地扭转了其二战中侵略东南亚的负面形象,获得了沿岸国的信任。在应对索马里海盗威胁方面,日本通过了《应对海盗法》,向索马里派出舰艇和飞机开展反海盗巡航,同时向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等提供反海盗资金支持,向索马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三)海洋可持续发展:占据道义高点,争夺国际话语权,引导标准制定
日本强调自身“海洋国家”定位,积极在国际合作与双边交往中宣传自身贡献,塑造“守护海洋的国家”形象。同时,日本还不时抛出自身方案,推广自身制度与标准。在2015年的亚太经合组织海洋渔业部长级会议上,日本主持“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资源的影响”工作组报告,“获各方赞赏”。2016年,日本作为G7峰会东道主积极推广国内海运排放税及排放报告制度,介绍自身应对蓝碳的“先进经验”。在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议题上,日本从“追随者”摇身一变成为“先行者”,在国际与国内层面同时发力,推出多项举措,欲利用该议题在G20大阪峰会上争夺国际引领地位、展示日本的国际协调能力、抢夺标准制定权、宣传日本形象。
(四)新疆域:起步早、重科研、稳推进、慎投入
随着全球变暖,北极航道特别是东北航道通航条件改善,近几年日本对北极议题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2013年,日本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2015年发布日本国家《北极政策》,同年开启“深化北极研究”项目,重点是北极航道常态化运行的可行性及对环境的影响。2019年5月召开的海洋本部会议上,安倍强调北极是下阶段日本海洋政策的三大重点之一。从开始关注到真正在北极议题上重点投入,日本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在深海探索方面,日本一直处于国际领先位置。
四、日本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行为特点
第一,政府作为:财、情、人投入并重。日本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起步早、时间长,多年的经营与不断总结经验,使日本较为熟悉全球治理的规律和国际组织的运作特点。日本在提案、协调、人才等方面深度参与,善于在双边、多边合作中宣传日本贡献、推介日本方案,也善于创造平台、扩大日本影响、把握主导权。为了显示其“经济大国”地位、实现其“政治大国”诉求,日本在大多数国际组织中承担着较高的会费。另外,日本经常在外交中打“感情牌”。在国际涉海人才培养上,日本既重视英语与学历教育,更注重人才专业化培养,如依托“日本海洋创新国际财团”项目培养涉海专业人才。在人才选拔中,相关省厅不仅及时发布国际组织详情、空缺职位信息,还在媒体上刊载在国际组织任职人士的履职心得,力图打“感情牌”以吸引高端人才。在人才输送上,日本强调领导岗位与专业职位并重,选派官员、学者、大学生分赴适合岗位。第二,官民一体:将智库纳入决策体系,产学研协同推进。二战后在日本重新寻求“海洋国家”定位的过程中,学者、智库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1世纪以来,以笹川和平财团海洋政策研究所为代表的智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交了《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书》《海洋政策大纲》《海洋基本法案概要》等多份研究成果和政策报告,它们直接构成了日本《海洋基本法》的蓝本。国家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成立后,智库、专家随即成为日本海洋决策体系的一部分。在争夺新疆域与海洋科技高地过程中,日本行为模式也呈现出产学研一体化特点。日本政府在前期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和制度支持,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学界共同参与,为最终的“商业化”铺路。第三,注重落实:细化时间表、路线图、任务清单。2008年开始,日本每五年出台一期《海洋基本计划》,对《海洋基本法》进行细化、深化,为日本海洋事业的发展规划落实路径和制定中期发展目标。2009年以来,日本每年出台一期《年度报告》,对《海洋基本计划》目标进行再拆解以及跟进、总结。从而构成了从《海洋基本法》顶层设计,到《海洋基本计划》设定中期目标,到《年度报告》逐年落实的逻辑闭环。
END
编辑 | 韩 茜
排版 | 张启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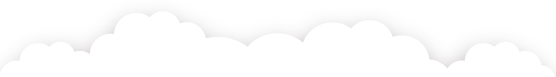

“武大边海”是边界与海洋问题最专业的信息平台
推送最新边海资讯、边海观察,发布边海问题专家观点
面向公众普及宣传边海知识
微信投稿邮箱:cictsmr@whu.edu.cn
“武大边海”独家授权转载《边界与海洋研究》期刊论文
期刊投稿邮箱:bjyhyyj@whu.edu.cn
编辑部联系电话:027-68753503
《边界与海洋研究》国内邮发代号:38-455
国际邮发代号:C9291
更多资讯请关注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官网:
http://www.cibos.wh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