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武大边海”直接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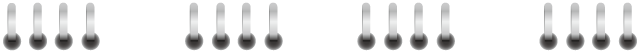

澜沧江—湄公河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本文作者
吕 星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副教授
王万英
云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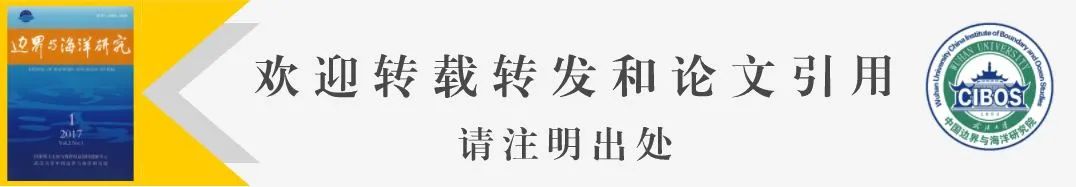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1期,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原文下载链接。

美国政府、智库、民间组织借2020年极端气候之机,误导媒体,炒作中国上游澜沧江水资源开发导致下游干旱,试图激化澜沧江—湄公河上下游国家水资源利用的矛盾,实现自身的地缘战略目标。本文以越南湄公河三角洲、越老柬共享的“三河”流域、柬埔寨洞里萨湖和泰国东北部呵叻高原水资源利用为例,探究水资源利用的历史、现状和问题,揭示湄公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的实质。
一、越南湄公河三角洲: 内部问题外化
湄公河三角洲总面积590万公顷,其中越南占68%,约400万公顷,占其国土面积的12%,居住着越南全国19%的人口,生产着全国50%的稻谷、65%的水产品和70%的水果,承担着95%的稻谷和60%的水产品出口,是世界最高生产力的三角洲之一,对于越南社会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经历了3次大的开发。1867年法国殖民者控制越南,引进蒸汽动力开挖河渠,开垦农田,种植水稻,从1890年到1930年,耕作农田增加了4倍多,达到200万公顷,人口从1860年的50万迅速增长到1930年的400多万。1957年以后,南越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实施“湄公河三角洲开发计划”,继续开发湄公河三角洲。1975年越南统一,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政府鼓励大面积种植水稻,特别是1986年以后,越南实施“革新开放”,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三角洲迎来了第三次大规模开发,农业用地扩大到320万公顷。
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开发成就与问题并存。三角洲大部分地区海拔仅0-4米,多地河流冲积物厚度超过100米,南部地区受到海水自然倒灌入侵,7个地理分区中有4个属于季节或全年水淹区。3次大的开发彻底改变了三角洲原有的生态系统,大幅降低了蓄水能力和季节调节能力,增加了系统的脆弱性,气候变化加剧了上述问题,威胁着湄公河三角洲的可持续发展。
发达的人工河网有利于雨季洪水下泄和旱季的海水倒灌,地下水超采导致每年地面下沉1.1-2.5厘米,比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仅为每年几毫米)影响还大,河道采砂和河流泥沙减少导致河岸渠岸的坍塌。但是越南政府和学者在对外宣传上,刻意忽略内部问题,将湄公河三角洲问题外部化,将三角洲的问题归因于气候变化和上游水资源开发利用,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二、柬埔寨洞里萨湖:
渔业管理的效率与公平困境
柬埔寨的洞里萨湖是湄公河的“心脏”、柬埔寨的“鱼仓”,它不仅是湄公河上的天然水库,调节着河流的洪枯,保护着湄公河三角洲,也贡献着柬埔寨60%的野生捕鱼量,直接与柬埔寨20%人口的生计相关。
洞里萨湖位于柬埔寨冲积平原中心,雨季湄公河河水上涨,流入洞里萨湖,湖面比旱季扩大3-6倍,旱季湄公河水位下降,湖水回流湄公河,完成一年的循环,学者称之为“脉冲式生态系统”。洪水携带鱼卵和营养物质,与湖滨带表面及季节性红树林一起为鱼类提供最佳的生长环境,使洞里萨湖成为世界淡水渔业生产力最高的水生生态系统之一,年野生捕捞量估计为1万-25万吨,至少生活着296种鱼。
洪水退去后大面积的湖滨带是重要的农业资源,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在湖滨带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凸显,吸引了外来及本地的投资者参与开发,结果是湖滨带退化,直接威胁着鱼类的生长环境,不合理的资源利用对脉冲式生态系统威胁更大。
在2000年以前,洞里萨湖渔业管理一直沿用法国殖民者的管理办法,将水面划分为35个商业捕捞区,通过市场拍卖捕捞权,10月至次年5月为商业捕捞期。经民间组织、学者和国际组织的多年呼吁,政府逐渐将捕鱼区划分给周边社区,截至2013年成立了516个社区捕鱼区。
将商业捕鱼区转变为社区捕鱼区旨在让周边广大的渔民从中受益,促进扶贫,避免不公平。但这种转变也增大了管理的难度和制度成本,带来了很多问题,诸如官员寻租,利益被地方精英攫取,很多社区成员并未真正获利等。方式的转变使洞里萨湖的渔业管理陷入了效率与公平的困境中。
三、“三河”问题:
对国家实力、能力和协调机制的综合考验
“三河”是指桑河、斯雷博河、公河3条河,由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共享,是湄公河最重要的支流,贡献湄公河18%的径流量,支撑着重要的农业和渔业,水电资源丰富,已建、在建和规划的水电站40座,位于越南境内的最多。其中越南在桑河上建设的720兆瓦亚力电站,于1999和2000年突然开闸大量泄水,造成柬埔寨沿河居民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三河虽是三国共有的国际河流,但对于负责跨境水资源问题的湄公河委员会而言三河属于支流,不属于其职能范围。越南和柬埔寨政府为此而设立的工作组未能及时处理跨境影响问题。在国际民间组织的支持下,柬埔寨民间组织、沿河村民和地方政府成立了“桑河保护协作网络”,开展研究、倡导和示威等活动,向柬埔寨政府施压。
关于桑河问题的冲突与协调机制,柬埔寨学者认为,越南具有上游优势,其实力比柬埔寨强,在双方的对话和谈判中柬埔寨均处于不利地位,不能有效规制越南的行为。而柬埔寨缺乏有效的水文数据和开展科学评估的能力,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越南很容易以柬埔寨的申诉没有科学依据予以反驳。1995年湄公河协定本身并不完善,存在缺陷,在这个协定中,支流的水资源开发只需要履行通知义务,不用履行事前协商程序。
四、泰国呵叻高原:
政治对水利建设的影响
呵叻高原位于泰国东北部,总面积15.5万平方公里,占泰国国土总面积的30%,其人口占全国的33%,其GDP占泰国的10%,人均收入只有曼谷地区的41%,全国平均的71%,是泰国贫困地区。呵叻高原同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竞技场,由于人口比例大可以影响选举结果,这里成为泰国政党争夺选票的重要区域。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泰国建构起来一套“水利使命”的话语体系,即它影响着决策者、规划者和大众的思维方式,指导着国家的决策。呵叻高原是一个干旱、生产水平低、落后和贫穷的地区,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水资源,没有农业灌溉就不可能发展农业,没有农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不可能摆脱落后和贫困状况。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启动“蓄水池计划”,建设小型水利设施,60年代皇家灌溉局认为实施和管理中小型灌溉项目代价较高,开始考虑大型水利设施项目,70年代中期又回归小型水利设施,80年代则提出大型跨流域调水计划,本世纪初提出“大水网计划”,拟从老挝调水。70年来的“水利使命”并没有改变呵叻经济落后的面貌,倒是给人们提供了值得反思的案例。
学者们从推动世界各地水利建设动力的角度分析认为,存在一个“铁三角”的利益强化机制,即政治家、官僚机构、项目建设及私人企业三方各有自己的利益,泰国也不例外。政治家为了获得选票,必须为投票人带来实际的利益,在广大的农村投资水利设施是比较好的政治投资,而恰恰呵叻地区持有全国三分之一的选票,政治家有持续的动力为之;官僚机构则因此有项目和预算,从而增加机构的权力和影响力,在泰国有不同的官僚机构竞争水资源开发权,如皇家灌溉局、国家能源局与环境自然资源部等;项目咨询公司和建设者通过源源不断的合同带来直接的经济利,其中,大型农场主往往是国家补贴水利设施的受益人。
从上述4个具体的实例可以看出,湄公河流域不同区域的水资源利用问题是复杂的,既有自然因素的影响,更有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及其治理能力的因素,并不是简单的“上下游关系”,或中国的问题。这也给澜湄水资源合作提出新的合作方向,现阶段应该以洪旱灾害预防与管理为主,下一阶段应该集中于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最终建立全流域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END
编辑 | 付姗姗
排版 | 李 阳


“武大边海”是边界与海洋问题最专业的信息平台
推送最新边海资讯、边海观察,发布边海问题专家观点
面向公众普及宣传边海知识
微信投稿邮箱:cictsmr@whu.edu.cn
“武大边海”独家授权转载《边界与海洋研究》期刊论文
期刊投稿邮箱:bjyhyyj@whu.edu.cn
编辑部联系电话:027-68753503
《边界与海洋研究》国内邮发代号:38-455
国际邮发代号:C9291
更多资讯请关注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官网:
http://www.cibos.wh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