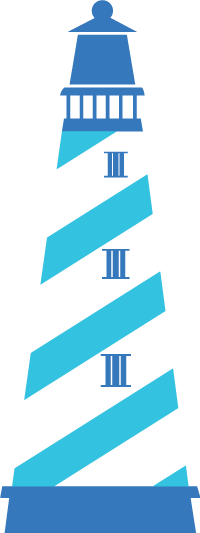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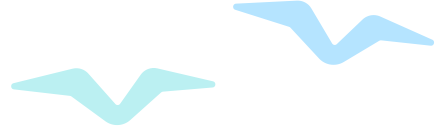

点击上方“武大边海”直接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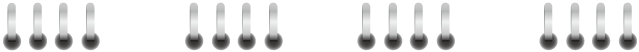

美国军舰闯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范围内
图片来源:环球网
本文作者
杨力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助理、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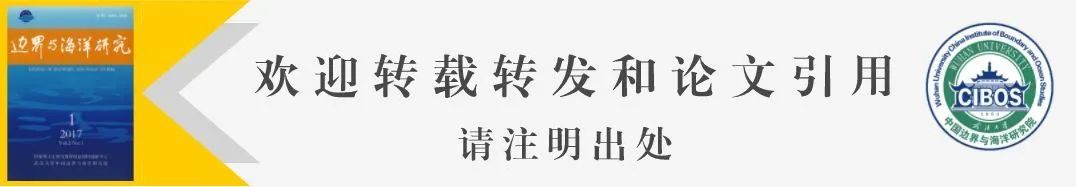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4期,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原文下载链接。

一、航行自由作为国际法原则与规则的内涵及其相对性
(一)航行自由作为国际法原则的形成与演变
航行自由是海洋自由最主要的要素,而海洋自由则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原则。17世纪初期,格劳秀斯发表的《海洋自由论》,从自然法、国际法等角度,包括海洋广阔无垠、流动的物理特性使其不可能被占有以及各国之间交往和贸易的实际需要等,系统论证了海洋自由原则。理论上,“海洋无法被占有”的观念只是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随着技术的进步,海洋的“不可占有性”和“不可枯竭性”都不太站得住脚,唯有国际贸易和交往的需要被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因此,公海自由不是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而是附属和依赖于商业和交通权利等其他的法律规则的。
海洋自由之所以能成为国际公认的法律原则,一方面是因为它顺应了人类交往和互通有无的根本需求,符合主权国家林立的国际社会现实,因而在全球化作为主要特征的当今世界,包括航行自由在内的海洋自由原则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与世界主要海洋大国特别是新兴海洋大国的持续推动密不可分,因为包括航行自由在内的海洋自由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利于海洋大国特别是新兴海洋大国的法律规则。
(二)航行自由作为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主要内涵
航行自由原则的主要内涵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中得到明确的阐述。《公约》第87条第1款规定,“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第90条规定,“每个国家,不论是沿海国和内陆国,均有权在公海上行驶悬挂其旗帜的船舶”。从这个意义上说,航行自由原则不大可能受到任何国家的公然挑战,航行自由作为一项被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的地位不会轻易动摇。在具体规则层面,航行自由最主要的保障和体现是船舶的船旗国管辖制度,亦即除其他国际条约和《公约》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形外,船舶在公海上仅受船旗国的专属管辖。军舰则在公海上有不受船旗国以外任何其他国家管辖的完全豁免权。
(三)航行自由原则在国际法上的相对性
作为法律规则,航行自由的适用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较强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航行自由原则的发展具有相对性。海洋自由原则逐渐获得国际公认的过程,与主权国家不断扩大管辖海域范围的历史进程大体同步。两者虽有对立的一面,但均符合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和发展趋势,因此得以相伴相生,也必须协调共存。有的国家兼具海洋使用国和沿海国身份,因此在同时维护航行自由和推动扩大国家管辖海域范围两方面形成矛盾但又协调的统一。
第二,航行自由规则具有权利和义务上的相对性。国家根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自由和权利,必然也受到国际法规则的规范和限制。从具体的管理制度上来看,公海的航行自由受到普遍管辖权和船旗国管辖权的限制。
第三,航行自由原则的具体运用因国因时而异。航行自由原则的应用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根据多样化的政策需要,航行自由原则被阐释和运用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二、美国航行自由政策和实践的若干特点
(一)美国将航行自由视为国家根本利益
美国从其价值观念、历史经验和战略需要出发,不仅将航行自由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甚至进一步将航行自由本身视为国家的一项根本利益。维护航行自由不仅是美国独立以来外交政策的一项核心诉求,也是美国海军的三大根本任务之一(另两项是维护、训练、装备海军力量和阻止侵略)。这种国家利益定位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并不多见。与其他各国区别不大的是,美国维护航行自由当然有经济层面的考虑,包括确保国际贸易通道的畅通等。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要想维持“全球领导地位”,必须要确保其军事力量的全球机动性。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理念,包括战略灵活性、海外存在和力量投射等,均依赖于传统的航行自由。
(二)美国对《公约》的解释和运用带有鲜明的实用色彩
美国迄今没有批准《公约》,但又经常以《公约》为依据捍卫航行自由利益,反映了美国对待《公约》的实用主义态度。
美国认为《公约》在传统海洋利用上达成的“利益平衡”实际上是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反映。美国虽未批准《公约》并不妨碍其援引《公约》有关规定和其认定的习惯国际法来维护自身关于航行自由的立场。不过,美国积极提倡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概念,强化国际水域(international waters)的提法,将上述领域作为自由开展军事活动的舞台,这两个概念似已成为美国维护航行自由立场的主要依托。
但是,《公约》并未使用“全球公域”与“国际水域”这两个表述。尽管《公约》在公海有关条款的制订上留下了灰色地带,但与上文分析的航行自由原则在适用范围上的相对性相呼应,似乎可以初步判断,《公约》在国家管辖海域与公海之间存在自由开放程度上的多层次、渐进式过渡,以及沿海国和非沿海国之间的多元化利益分配。《公约》的“公平的平衡”恰恰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精细、微妙的规则体系基础之上的。而美国主张的领海之外即为国际水域这样的简单二分法,不仅在《公约》条款中找不到明确依据,而且似乎也并不符合《公约》背后反映的“利益平衡”精神。
(三)美国“航行自由计划”以法律目的为初衷,但其政策性日益突出
美国维护航行自由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将美国对航行自由规则的解释和适用转化为国际通用的法律标准。1979年开始实施的“航行自由计划”及相关的“航行自由行动”,就是美国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一项政策措施。美国“航行自由计划”具有明确的、特定的法律目的,即挑战美国所认定的其他国家的“过度海洋主张”,避免有关主张因为默认而取得合法地位。美国“航行自由计划”主要通过三个手段实施:外交抗议、与沿海国代表的磋商以及在处于过度海洋主张之下的海域开展军事行动。由此可见,“航行自由行动”是“航行自由计划”的执行手段之一。
三、中国与美国在航行自由问题上的分歧
中国与美国围绕航行自由问题的争执,主要集中在南海等中国周边海域。就法律原则而言,中美双方在尊重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并无分歧。但综合考察双方的法律和外交实践,两国对航行自由的具体认知确实存在差异,双方的分歧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领海内外国军用船舶是否可以行使无害通过权的问题。尽管领海内的“无害通过”与“航行自由”在国际法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美国仍然将挑战中国法律关于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国领海须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规定纳入到其“航行自由行动”挑战的目标之中。
二是领海基线的划设问题。美国对中国于1996年公布的大陆领海部分直线基线和西沙群岛直线基线以及2012年公布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直线基线均持有异议。
三是在专属经济区及其上空军事活动的合法性问题。引发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的,是美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及其上空开展的军事侦测活动。
四是中国南海海洋主张的“合法性”问题。美国不是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端的当事国,但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声明和报告等,对中国的南海断续线主张提出了质疑和否定,对中国以南沙群岛整体及其单个岛礁为基础主张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提出了异议。
美国关切的核心,是中国会将南海变为“中国湖”并将美国排除在外,航行自由成为美国抵制这种倾向的法律武器和政策工具。
中国关切的核心,则是美国通过对南海事务的干预损害中国周边的政治和安全环境,牵制中国的发展,倾向于认为航行自由只是美国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一个借口。
中美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负面解读,推动双方在航行自由问题上的矛盾螺旋式上升,因近距离接触导致擦枪走火的风险有所增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两国要想彻底解决在航行自由问题上的分歧恐怕不是易事,如何管控有关矛盾是双方战略界和法律界需要认真考虑的重要课题。
四、结语
航行自由原则从来不是孤立和抽象的存在,总是与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竞争互相联系,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关于中美之间的航行自由问题,双方可以通过法律、战略(政策)和海上管控三个层面的沟通,来努力管控矛盾,缩小分歧。
法律上,中美可首先确认在坚持国际法上的航行自由原则方面不存在根本分歧,并尽可能从全球视野和长远角度出发寻找利益契合点,开展务实合作。对于具体法律规则在解释和适用上的不同观点,可由双方的法律官员和学者进行持续、深入的讨论,以期逐步缩小分歧。
在战略(政策)层面,双方也可以利用一轨、二轨等渠道进行机制化的坦诚沟通,尽量减少互疑,避免误解和误判。
在海上管控方面,双方应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守住不冲突或防止意外事件升级的底线。这三个层面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可能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稳定的轨道。
END
编辑 | 韩茜
排版 | 李阳


“武大边海”是边界与海洋问题最专业的信息平台
推送最新边海资讯、边海观察,发布边海问题专家观点
面向公众普及宣传边海知识
微信投稿邮箱:cictsmr@whu.edu.cn
“武大边海”独家授权转载《边界与海洋研究》期刊论文
期刊投稿邮箱:bjyhyyj@whu.edu.cn
编辑部联系电话:027-68753503
《边界与海洋研究》国内邮发代号:38-455
国际邮发代号:C9291
更多资讯请关注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官网:
http://www.cibos.whu.edu.cn/

